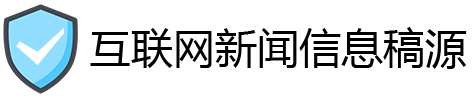岳立功
收到深圳出版社寄來尚飄著油墨清香的新書《風雨武陵山》,封面赫然撲來個熟悉的名字——孫健忠,心中漾起的欣慰伴隨著深深的刺痛。翻開書頁,鄉情鄉音,風聲雨聲,湘西人事浮凸熙攘而來。海邊閱讀,我不聞濤聲,卻似步入湘西空山,曠野無人,聽到了洛塔巖遠處陽雀泣血的啼唱,很想哭。
孫健忠是公認的“土家族人文文學奠基人”。他著作等身,文字詩性而樸素,人物地道鮮活,對鄉土對人性的思考深刻。但他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風雨武陵山》卻一改往日風格,“自廢武功”,用平實冷峻的筆調坦露了一段近半個世紀兵荒馬亂的日子,字字是血是淚——孫健忠最后的歌依舊是獻給故鄉,獻給那片他如此深愛卻如此多災多難的土地。
孫健忠是湘西土家族人,雖曾為省作協主席,全國人大代表,但相信一定也遭遇過前輩沈從文遭遇的外地人對湘西的誤讀。由于歷史的偏見,也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些小說、電視劇等對湘西認知上的誤導,讓外界對湘西的整體印象形成偏見,總以為湘西天生就是一個出土匪的地方,月黑殺人風高放火,充滿了恐懼感,這種偏頗的認知極度傷害了湘西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這一點,健忠應該深有體會,所以決心寫出湘西真實的歷史,為湘西祛魅,正名。他的祛魅,正名,就是求真寫實,甚至“去虛構”地告訴人們那一段歷史的事實和成因。湘西就是這樣,你自己去讀去體味這方水土這方人的隱痛和孤獨吧。
《風雨武陵山》選取了龍山這個武陵山下典型的土家族聚集地為故事發生地。龍山位處湘西東北角隅,與湖北交界。如果說當年的湘西是“中國的盲腸”,那么龍山就是這盲腸快要潰爛脫落的尾巴。在故事發生的年代,民國肇始,軍閥連年混戰,角隅龍山幾乎是權力真空地帶,自然是“城頭變幻大王旗”,“亂世英雄起四方”。孫健忠在全書中一改早中期的詩性表達和中后期的夸張變形風格,用冷峻的筆觸,寫實地呈現了當時當地的人事“匪事”根由,甚至完全用真實姓名記錄了師興吾,師興周,瞿伯階、瞿波平、彭春榮(叫驢子)等人由民入“官”入“匪”,時“官”時“匪”魚龍變代的種種不同緣由,以及經多方勢力角逐撕扯而導致的曲折經歷和最終歸宿,繪制了一幅生命百態圖。文本看似平淡,卻入木地寫出了美麗的高高武陵山被玷污和坍塌的悲苦歷程,令人透背涼。
當時角力于龍山的武裝部隊主要是“湘西王”陳渠珍的筸軍,湖南省主席何健的國軍,賀龍的紅軍,還有各處散落著的大小各色的“土匪”部隊。“土匪”在湘西其實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歷史存在,匪禍與民變也常在毫厘之間。作者在該書中最先提到的“匪”是內七棚寨秀才族長師興吾,其村鄉場遭湖北來鳳土匪搶劫而起恃武保家之念,攜煙土拜訪“川東一霸”周矮子,得辰溪造二十支,成功自衛。為求“長治久安”,師興吾又攀附上了“湘西王”,成為湘西巡防軍中校營長。由自保而逐利,師興吾謀殺了召頭寨鄉長。該鄉保安隊長瞿伯階感到人心難測,于是拖槍上山為“匪”。師興吾病逝把權力交由師興周接手。剛愎自用的師興周卻不聽,被賀龍打得潰不成軍。瞿波平因愛情失意而投奔族兄瞿伯階,成為其得力助手和接班人。作品充分揭示了湘西之“匪”復雜而特殊的歷史存在,往往身份與臉譜多變難定。《風雨武陵山》不是從傳統“剿匪”的角度寫“匪”,而是從“匪”的內部深拓,用平實的筆調寫出了湘西匪患的種種由來及其多面性,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也是一種全面的創新。
臨近解放,解放軍大軍壓境,國民黨中統軍統四處流竄拱火,謠言象黑翅膀的蝙蝠滿天亂飛。每個人都如草芥被推攘裹挾,其命運也像翻燒餅般并不能完全由自己選擇,成王成寇常在毫粒之間。師興周曾被國軍作為匪首關在耒陽四年,后又在“龍山人治龍山人”的謀略下東山再起成為國軍師長,開始圍剿宿敵瞿伯階。被圍剿的瞿伯階、彭春榮兵敗烏龍山后反攻龍山尋仇未遂,彭春榮被打死。瞿伯階走投無路之時卻遇到“神秘人”,搖身一變反倒成了國軍暫十師師長,風光一時,不巧卻在去搶割罌粟時偶感風寒不治身亡,接手的瞿波平任代師長。沒幾天,解放軍進剿,師興周投誠。瞿波平四處亂竄,被打得幾乎成了光桿司令的時候,偏巧竟意外收到陳潛的一封信——他接受了改編,修成正果。文章的結尾是瞿波平“心潮難平”地赴省城見程潛主席。作者意味深長地寫道:“哦,新的一天開始了!公路兩旁,連綿無盡的油桐樹,綻放著朵朵如雪的花簇。但不知這條鋪滿花簇的道路,是通往一個怎樣的未知的神秘世界?”這段話不完全是當事人心境的特指,我想更多的是作者對人生的深刻思索。
初讀文本,我驚訝健忠為何要完全放棄過往的詩性風格,放棄他高超的虛構和魔幻變形才能,寫下這么一堆“史料式文字”?后來我想,湘西那一段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完全是比馬爾克斯的魔幻更魔幻更荒唐的現實啊!健忠也許覺得,如果再去虛構或魔幻一通,反倒會畫虎類犬,狗尾續貂。只因那一段歷史太奇特太魔幻,也許作者自己也沒能找到完整的答案,他應該是有一種緊迫感:如果不抓緊把這些東西原生態記錄下來,也許從此就全湮滅了。感謝健忠為我們記錄下了那一段復雜的、沙泥俱下的湘西真實存在。在文本中,健忠沒有站在上帝的視角去對每個角色作道德定位和評判,每個讀者卻從中能得到不一樣的獲益。
健忠長我幾歲,是我的老師,但他待我如朋友如兄弟。健忠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所有電話都由他的夫人接后遴選,有幸,我總是能接通本尊的。每次去長沙,他都要設家宴款待,無話不談。健忠的創作幾乎是不與他人合作的,但卻與我合作過電影、電視連續劇和長篇紀實文學的。我的創作完全是與他的提攜鼓勵相關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還在鳳凰吉信鄉下教書的我,只不過發表了幾首小詩,一兩篇散文,籍籍無名,但第一次相見交談后,他便邀約我和他合作寫電影劇本,這真的讓我受寵若驚!他的信任與鼓勵是我志立一生寫作的恒久動力。我在長沙出版了“湘西三部曲”的第一部《黑營盤》時,時仼省作協主席的他便高度評價是“湖南文學的可喜收獲”,并打算為之召開研討會,遺憾的是,我當即調去了深圳。此事雖沒了下文,但他的鼓勵一直鞭策著我在其后的三十年間無論遇到多少波折,也勇毅地堅持把《湘西三部曲》寫下去。
健忠具有典型的湘西人性格,敢愛敢恨,人稱“孫大炮”。這種耿直也讓他吃過不少苦頭,但這個湘西漢子是壓不垮的。健忠有創作天分,更是個創作苦行僧。他體驗生活是拖家帶口扎根洛塔巖,真切體驗民間苦樂。寫作于他是神圣的。他的寫作習慣是封閉門窗,白天當作夜的黑。在那個仄逼的小空間,他苦苦求索,狼一樣地來回踱步,轉圈,偶有所得,便趴下來奮筆疾書,爾后又是轉圈轉圈。所以,他的文字看似樸實無華,實則字字珠璣,有思想深度。他的名作《甜甜的刺莓》,尤其是《醉鄉》反映改革開放,卻不是唯美的“田園牧歌”,寫出了湘西人的勤勞質樸勇敢,更表現了大變革中的人性變異,心靈碰撞,寫出了作家對故土前景的憧憬和憂思。正如被改編成的電視連續劇主題歌所唱:“醉鄉那個不是富貴鄉,也莫道那嘩啦啦山泉流的是酒漿,昨日的悲,今日的歡,細細地品,慢慢地嘗,幾分醉,幾分醒,幾分淡淡憂傷,哦,我們土家是醉鄉!”健忠書寫湘西鄉土,卻不因循守舊,具現代意識視野。他的《死街》用變形手術刀,生動深刻地剖析了湘西人的性格基因和歷史宿命,是一部民族寓言式的杰作。
雖然他的創作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健忠還有更大的“野心”。他跟我說過想寫歷代土司王朝,寫湘西的大歷史,為此還作了很長很深入的調查采風和構思準備。也許是后來身體方面的原因,也許是當“官”牽扯了較多的精力,又或許因“大炮”性格而涉入了一些無謂的人事糾纏,他的湘西大歷史寫作最后只得了這部《風雨武陵山》的絕唱,真的是留下了遺憾。雖然只是這么一部不算太厚的著作,我們卻不難從中讀到他對湘西故土的愛,他的責任感緊迫感,他的思考,他的宏愿。他寫下這部作品,明顯是經過總結和反思后的新起點。他歇住了魔幻的翅膀把爪子重新落回到扎實的土地上,但不是回到過去的寫作,而是用自己感悟到的全新觀念去重新透視這塊土地。他勇毅地突破了自己的“囚籠”,嘗試涉獵某些“雷區”,將觸須探進某些諱莫如深的領域。以往的創作都是過濾過的自來水,這一回他抽掉了篩子,掬捧山泉,雖前景未卜,但一往無前。他直寫“匪事”,直寫人性,這種寫法不能代表創作的全部,但卻為傳統的湘西書寫拓展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作品由于種種原因雖說未臻成熟,但它的問世是湘西書寫的重要收獲,也必將產生長遠的影響。
《風雨武陵山》的問世,昭示了由沈從文、孫健忠等前輩開拓的湘西文學書寫,在一代又一代湘西作家的傳承接續下,將前景廣闊,碩果累累。美麗湘西也會以更全面更真實更絢麗多彩的風姿熠熠生輝,照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