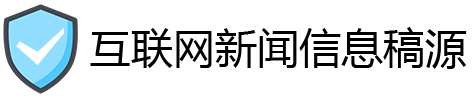丁竹林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與沈從文先生有過一次書信來往。沈老的親筆回信,我至今一直珍藏在身邊,算來已有四十余個(gè)春秋。如今,沈老離我們而去,不覺已三十六年。其間,每當(dāng)細(xì)讀沈老回信,我的心情總是難以平靜。在他三十六周年忌辰,我寫下這些文字,以表達(dá)對(duì)沈老沉痛的追思,深深的懷念。
我自一九六五年秋起的十九年間,在湖南岳陽原省屬國營(yíng)錢糧湖農(nóng)場(chǎng)從事中學(xué)語文教學(xué)。教學(xué)閑暇,我常閱讀一些中外文學(xué)名著和國內(nèi)文學(xué)期刊,學(xué)習(xí)文學(xué)寫作,曾被原岳陽地區(qū)文聯(lián)吸收為該會(huì)文學(xué)工作者協(xié)會(huì)會(huì)員。
一九八〇年底,岳陽市文聯(lián)主辦的文學(xué)刊物《洞庭湖》,刊發(fā)了一篇沈從文的訪問記,我才知曉我們湖南,我們中國有這樣一位作家,而且這位作家已名揚(yáng)海外,而在當(dāng)時(shí)的國內(nèi),對(duì)他很少提及,國人知道“沈從文”其人其作的并不太多。
也就是從那時(shí)起,我總期盼能對(duì)沈從文有更多的了解,希望能盡早讀到他的作品。但在當(dāng)時(shí),他的作品及相關(guān)資料,能找到的渠道有限。我只好照著那篇訪問記披露的地址,以“故鄉(xiāng)一個(gè)陌生的無名晚輩”名義,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惶惶然給沈老寫了一封信。
沒想到,年事已高且學(xué)術(shù)研究工作繁忙的沈老,竟在那年三月六日從北京給我寄來了他的親筆回信。回信是用歷史研究所的便箋寫的,共三頁,用墨輕淡,字體為獨(dú)具風(fēng)格的毛筆行書。后來,我支邊新疆時(shí),得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老的小說、散文選集,便郵購了一套,其扉頁上影印的沈老文稿手跡,與那封回信的字跡一致,證明回信確系沈老手書無疑。
沈老在回信中寫道,“我所得于社會(huì)的已經(jīng)夠多,再不能以空頭作家名義面對(duì)社會(huì)。”談到中國文壇,沈老列舉了他心中的中國作家,講了只有怎樣去認(rèn)識(shí)、對(duì)待文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批評(píng),才不至于犯錯(cuò)誤。
信的末尾,沈老對(duì)我進(jìn)行了叮囑和告誡,可謂苦口婆心。
整篇信件,字里行間,既包含著沈老當(dāng)時(shí)莫可言狀的辛酸、苦楚,又隱含著不可折服的自信、倔強(qiáng)與自嘲自解。但是從中又可以讀出,其報(bào)答人民、報(bào)效社稷的初衷依舊,癡心未改。
沈老對(duì)我這個(gè)素昧平生的無名晚輩,如此無所顧忌地敞開心扉,傾吐衷腸,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不知道,是老人衷腸無從傾訴,還是濃濃鄉(xiāng)情牽起了他的無限傷感?抑或是為不讓故鄉(xiāng)晚輩,對(duì)他生出誤解?具體情況,我不得而知。
此后,我不敢,更不忍心去信打擾沈從文先生,因?yàn)樗先思易钚枰氖菚r(shí)間和寧靜。
一九八五年,我支邊舉家去到新疆,迢迢萬里,關(guān)山阻隔,沈老的情況,就再也無法打聽,無從知曉。
直到一九八八年六月初,我在辦公室的《人民日?qǐng)?bào)》上,看到《深感于沈從文之逝世》這篇短文時(shí),才驚悉沈老已于五月十日晚因心臟病突發(fā)與世長(zhǎng)辭。得知這一消息的我,既錯(cuò)愕又痛心不已,痛心失去這樣一位可親可敬的作家。
當(dāng)時(shí),我急切地想知道沈老的后事是在哪里、又是如何辦理的,想知道對(duì)他是如何“定論”的。我凝神佇立,翹首南望,想到了沈老的家鄉(xiāng)——那遙遠(yuǎn)的湘西鳳凰,于是向鳳凰縣相關(guān)方面寫了一封長(zhǎng)信。
八月二十四日,鳳凰縣“沈從文文學(xué)社”回信告知,鳳凰縣各族人民,滿懷著對(duì)沈老的崇敬和懷念之情,舉辦了各種形式的祭奠活動(dòng),一批具有紀(jì)念意義的事項(xiàng),亦正在規(guī)劃或施工當(dāng)中。遺憾的是,我想知道的某些內(nèi)容,信中未能提及。具體原因,我不得而知。
如今,這些我曾想知道的內(nèi)容,沈老用其作品的持久影響力給出了回答。
古往今來,在浩如煙海的文學(xué)作品中,凡歷經(jīng)歲月滄桑變化,仍為本國乃至世界億萬讀者接受、喜愛而經(jīng)久不衰的作品,我想,皆可謂之傳世之作;能對(duì)一個(gè)國家,一個(gè)民族的歷史文化,或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領(lǐng)域,鍥而不舍,潛心研究,撰寫出極有價(jià)值甚至填補(bǔ)空白的專著,我認(rèn)為,那即是對(duì)國家、對(duì)民族的一大貢獻(xiàn)。
而沈老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以此報(bào)答他深愛著的祖國、民族和人民。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他自一九二四年發(fā)表第一篇作品步入文壇,至一九四九年改為歷史文物研究,筆耕不輟,出版小說、散文、自傳和通信各種集子八十余種,近五百萬字。這些作品,已成為中國文學(xué)寶庫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