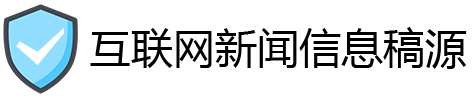李詩好
暮色四合時(shí),我踩著斑駁的樹影回到野雞巖。老槐樹的枯枝在晚風(fēng)中輕輕搖曳,像要拂去我肩頭積了多年的風(fēng)塵。寨口曬谷場(chǎng)空蕩蕩的,石碾凹槽里積著昨夜的雨水,倒映著幾片槐葉。青灰色石板路蜿蜒依舊,卻再不見當(dāng)年嬉戲追逐的孩童,只剩坍塌過半的臥牛石,在暮色里固執(zhí)地守望。
野雞巖寨蜷在代朝山腳下,距湘西浦市古鎮(zhèn)不過十里。寨后山崖上臥著塊灰褐色巨石,巖頂平如曬谷場(chǎng),常有些野雞在此棲息,“野雞巖”的名字便由此而來。
記憶里,破曉總有三兩只野雞立在巖頂啼鳴。最神氣的是那只雄雞:銅綠色的頸羽流轉(zhuǎn)著晨光,赤銅色的胸脯點(diǎn)綴著黑斑,長長的尾羽掠過朝霞時(shí),石壁上便投下斑斕光影。老人們說,這些野雞是山神的信使,啼鳴能驅(qū)散瘴氣。如今巖體坍塌,裸露出黃褐色的斷層,巖縫里的石英結(jié)晶像凝固的淚滴,唯有那蓬野薔薇,還開著四十年前同樣鵝黃的花。
寨里三十多戶,除了一戶徐姓木匠,都姓李。李家大院的青磚門樓上,“耕讀傳家”的匾額金漆剝落,露出松木年輪。徐木匠打的雕花木床散落在各家,榫卯間的蠟色包漿,成了寨子里最溫潤的外姓印記。
記憶中的黃昏總從曬谷場(chǎng)醒來。大人們收谷的竹耙劃過青石板,“沙沙”聲驚起一群麻雀。我們幾個(gè)孩子常蹲在草垛后面,看小珍用鳳仙花染指甲,那抹紅在暮光中格外妖冶,像要把最后的陽光都吸進(jìn)去。“快看!草兒又尿褲子啦!”小兒舉著竹竿狂奔,草兒提著褲腰追趕,赤腳拍得泥水四濺。銀花和七妹蹲在溪邊偷笑,她們過家家的桐葉碗里,地枇杷泛著蜜糖般的光。
溪邊的捶衣聲在日落前最喧鬧。女人們卷起褲腿掄棒槌,水珠濺起七彩虹光。“小祖宗!衣裳又掛破了吧?”月英娘作勢(shì)要打,我們幾個(gè)泥猴立刻扎進(jìn)塘里,驚得鵝群撲棱棱飛起一片白浪。父親磨刀的“霍霍”聲從塘邊傳來,和著歸鳥的啼鳴,在暮色中譜成一曲獨(dú)特的鄉(xiāng)音。
“馬步要穩(wěn),出拳要狠!”方元爺沙啞的嗓門總在曬谷場(chǎng)上炸響。這個(gè)被土匪擄去三年的漢子,左耳缺了半邊,卻練就了一身本事。武兒學(xué)得最認(rèn)真,后來果真憑著功夫當(dāng)了武警。“哎喲!”小克捂著腿直跳腳。方元爺瞇眼笑:“這點(diǎn)痛都受不了?當(dāng)年我在土匪窩里,挨過真刀真槍呢。”
代見伯的煙袋鍋總要等啟明星亮了才點(diǎn)燃。這個(gè)參加過徐州會(huì)戰(zhàn)的老兵,皺紋里藏著彈片留下的傷痕。“那年我在徐州……”擺龍門陣時(shí),他總愛吐出個(gè)煙圈,煙霧中仿佛有千軍萬馬奔騰。草兒總在這時(shí)打瞌睡,腦袋一點(diǎn)一點(diǎn)像啄米的小雞。當(dāng)說到“薛仁貴一箭穿三重甲”時(shí),巖上的野雞突然驚飛,翅膀拍擊巖石的聲響,恍如沙場(chǎng)金戈交鳴。
“好崽,回家吃飯嘍——”母親的呼喚穿過時(shí)空,刺破暮色。這聲音驚起草叢里的蚱蜢,也驚醒了門檻上打盹的徐婆。“秀才回來了?”因我是寨里第一個(gè)大學(xué)生,這稱呼便成了我的“雅號(hào)”。她枯瘦的手指顫巍巍指向臥牛石:“自打銀花出嫁那年,一場(chǎng)暴雨塌了半邊,野雞就少了……”突然,一只野雞從亂石中竄出,羽翼劃出的弧光將黃昏劈成兩半——一半是當(dāng)年追著花轎的彩羽,一半是我此刻狂跳的心。
最后一抹夕陽從老槐樹梢滑落時(shí),寨里的燈火次第亮起,像散落的星子墜在墨色綢緞上。轉(zhuǎn)過山彎,又一聲“咯噠”追來,我沒回頭,任其在群山中蕩出綿長回響。這或許是野雞巖最后的道別——記憶的黃昏里,所有碎片突然蘇醒:母親喚歸的尾音,父親磨刀的錚鳴,小伙伴們永遠(yuǎn)年輕的歡笑,都隨著最后那縷陽光,悄悄隱進(jìn)了巖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