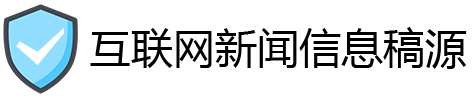—— 彭學(xué)明從《娘》到《爹》的敘事策略
姚復(fù)科
一
一個(gè)成熟的作家要完成一種風(fēng)格的質(zhì)變,需要契機(jī),甚至奇跡。如果文學(xué)是對(duì)復(fù)雜經(jīng)驗(yàn)的世界的超越,整合來(lái)表達(dá)一種獨(dú)特體驗(yàn)和認(rèn)知的話(huà),事實(shí)上,經(jīng)驗(yàn)世界本身是混沌的,是達(dá)不成自洽邏輯的存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就是在這混沌中達(dá)成邏輯自洽而構(gòu)建世界。以寫(xiě)散文而成名的彭學(xué)明,又一部歷史非虛構(gòu)小說(shuō)《爹》出版發(fā)行。我的感覺(jué)是一個(gè)作家足夠可以在自己熟悉園地精耕細(xì)作,不滿(mǎn)意了,拓展了自己的土地。從長(zhǎng)篇敘事散文《娘》到歷史非虛構(gòu)小說(shuō)《爹》,變化的是體裁,不變的是始終堅(jiān)持生活與歷史的非虛構(gòu)表達(dá)。
如果說(shuō)非虛構(gòu)意味著真實(shí),文學(xué)意味著可讀性和藝術(shù)性,那么這兩者之間本質(zhì)上是一個(gè)策略和技術(shù)的把握。真實(shí)的細(xì)節(jié)材料和歷史事件是非虛構(gòu)寫(xiě)作的佐證,文學(xué)性則決定了非虛構(gòu)作品是否生動(dòng)、能否成功走向公眾,是否具備優(yōu)秀作品的特質(zhì)。
二
我欣賞那些心懷故土的人。我敬重那些面對(duì)歷史和故土,坦陳自己卑微的表達(dá)。彭學(xué)明文學(xué)敘事是非虛構(gòu)的表達(dá),他始終以自身的經(jīng)歷介入現(xiàn)實(shí)而又實(shí)現(xiàn)超越的敘事策略,為他提供了馳騁田獵的可能,《娘》無(wú)疑完成了這種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之上的理性構(gòu)建和超越的完美。
《娘》的世界是生活的真實(shí),也是藝術(shù)的超越。彭學(xué)明在書(shū)中提到的他們母子流浪式的生活過(guò)的地方,對(duì)許多外地讀者而言也許就是湘西,也許就是一個(gè)模糊不清的地名概念。于我而言,一切不過(guò)是一個(gè)小時(shí)徒步翻越一個(gè)山嶺的行程。我兒時(shí)生活的村莊在峽谷平地上,我們從小把《娘》中的那些村莊通稱(chēng)為“界上”。在我印象中界上是片僅供活命的不毛之地,沒(méi)有我們峽谷里富庶,冬日里橫亙?cè)趰{谷山梁上的一條不化的雪線(xiàn),就是界上與河邊人家的區(qū)別。我這樣說(shuō),就是給我自己具備說(shuō)話(huà)資格的一個(gè)證明。《娘》的世界從物質(zhì)到心理,不止是書(shū)面的湘西世界,同樣也是最具現(xiàn)實(shí)色彩的湘西世界,而這現(xiàn)實(shí)的核心正是作者對(duì)生活經(jīng)歷或者說(shuō)是對(duì)經(jīng)驗(yàn)世界整合、超越之后的文學(xué)的表達(dá),美學(xué)構(gòu)建。也正是如此,置身于書(shū)面世界觀照娘,娘不只是書(shū)面的湘西的娘,同樣也是最具現(xiàn)實(shí)色彩的湘西人的娘。而最讓我感佩的,在這敘事策略之下,彭學(xué)明憑借自己藝術(shù)的思考、反省、自我解剖,實(shí)現(xiàn)了將特定年代下的一個(gè)個(gè)平凡鄉(xiāng)村從精神到物質(zhì),從民風(fēng)到人性的大超越。這個(gè)超越構(gòu)建下的鄉(xiāng)村成了作者成長(zhǎng)歷程的九九八十一難的記憶符號(hào),從這里開(kāi)始一個(gè)個(gè)村莊就成了“我”和娘的戰(zhàn)爭(zhēng)戰(zhàn)場(chǎng)。作者的寫(xiě)作是具有抱負(fù)和野心的寫(xiě)作,力圖通過(guò)“我”和娘的戰(zhàn)爭(zhēng),實(shí)現(xiàn)一個(gè)普通平凡的湘西的娘之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現(xiàn)實(shí)意義。為實(shí)現(xiàn)娘的道德化身和苦難化身的飽滿(mǎn)形象的構(gòu)建,在這一次次“我”和娘的戰(zhàn)爭(zhēng)中,“我”無(wú)可救藥的成了大逆不道的罪人。如果一部文藝作品只能讓閱讀者的感覺(jué)游離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之外,抵達(dá)不了人性含混蒙昧對(duì)立地界,這絕對(duì)不是一部好作品,容易暴露作者功力的缺乏。《娘》的鮮明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感、真實(shí)感恰恰證明了彭學(xué)明找到了文學(xué)的精神背景與現(xiàn)實(shí)生活背景一個(gè)有機(jī)的契合點(diǎn)。這是非虛構(gòu)文學(xué)表達(dá)特質(zhì)之一。
娘是實(shí)體的娘,也是精神的娘。我喜歡《娘》的寫(xiě)作自覺(jué),但更欽佩作者的誠(chéng)實(shí)與無(wú)畏。立足自己身世經(jīng)歷,把自己童年苦難、屈辱、掙扎、扭曲等無(wú)法刪除的記憶完成一次理性的構(gòu)建和超越。這是需要勇氣和膽量的。這種超越的結(jié)果,豐滿(mǎn)了精神世界的娘,娘由個(gè)性實(shí)現(xiàn)了共性的結(jié)合,娘就成了湘西的娘,成了世界的娘。娘堅(jiān)韌不拔的性格有著鮮明的湘西特性。這樣的母親在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jiàn),親切的如同湘西鄉(xiāng)下的每一個(gè)母親。
三
加西亞馬爾克斯說(shuō):“真實(shí)的記憶就像記憶中的幻影,而虛假的記憶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現(xiàn)實(shí),因此我無(wú)法分辨幻滅與懷舊的界限。”在此思路下,小說(shuō)體裁的《爹》的世界是真實(shí)的也是虛構(gòu)的,是幻影,也是現(xiàn)實(shí)。歷史的真實(shí),回歸本質(zhì)而言只有歷史觀的真實(shí)。
意大利文藝評(píng)論家克羅齊說(shuō):“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他根本論述在于說(shuō)明如下一個(gè)話(huà)題。過(guò)去的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xiàn)實(shí)的思索,打動(dòng)現(xiàn)實(shí)的興趣,和現(xiàn)實(shí)的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那么這個(gè)過(guò)去的歷史不構(gòu)成真正的歷史;相反,如果過(guò)去史在我的現(xiàn)時(shí)思想活動(dòng)中未能復(fù)蘇,那么這個(gè)過(guò)去歷史就失去了獲得它的歷史性。所以一切歷史都必是現(xiàn)時(shí)史,著重歷史的現(xiàn)時(shí)性,其實(shí)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lián)貫。于文學(xué)而言就是歷史的真實(shí)與超越,可以說(shuō)完成了歷史非虛構(gòu)表達(dá)。
《爹》是打亂了時(shí)間而濃縮了湘西父輩的集體群像。大多數(shù)作家對(duì)歷史都抱有一種宿命感和使命感,尤其是地方少數(shù)民族作家,對(duì)自身本土歷史的執(zhí)念,保持著特有的溫情和敬重,從來(lái)不會(huì)對(duì)以往的歷史抱有虛無(wú),反而力圖尋找一種希望和力量作力于當(dāng)下和時(shí)代。彭學(xué)明也不例外,他仿佛感覺(jué)到了,歷史似乎無(wú)法回應(yīng)今天的時(shí)代,沒(méi)有辦法建立起和時(shí)代的真實(shí)的關(guān)聯(lián),于是創(chuàng)作者需要轉(zhuǎn)換一種視野,去尋求非虛構(gòu)的可能性。
作為散文家的彭學(xué)明,具備自己獨(dú)到的觀察和細(xì)節(jié)描述功夫,在《爹》中得到了大量收放自如的運(yùn)用,作者熟悉湘西的近現(xiàn)代歷史,對(duì)民俗風(fēng)情了如指掌,加上多年用工夫采風(fēng)積累,他具備了恢復(fù)一個(gè)歷史時(shí)空框架的能力,以小處著力“反寫(xiě)”歷史宏大敘述的策略,彰顯了早年的散文寫(xiě)作的深厚功底,也飄逸出了散文體裁的拘束,奔馳于遼闊想象空域。于是作品超越了歷史意義上的唯一性和客觀真實(shí)性,取而代之的是明顯的虛構(gòu)化的特質(zhì)。在長(zhǎng)篇小說(shuō)《爹》中,作者為諸多湘西文學(xué)敘事的實(shí)踐中有同一性,時(shí)空架構(gòu)是重疊的,在歷史人物命運(yùn)的縱向上,復(fù)活了一個(gè)時(shí)代和社會(huì)生活的橫斷面,以此為坐標(biāo),觀照湘西地域文化、歷史和民族命運(yùn),賦予湘西民族歷史的時(shí)代關(guān)聯(lián),使之重獲歷史性。這雖然是一個(gè)作家普遍的共性,但依然不乏價(jià)值意義,比如小說(shuō)中的命運(yùn)感,人物命運(yùn)的執(zhí)著,看得出作者對(duì)于歷史人物具備的獨(dú)特理解。在文化意義上,爹這個(gè)人物即是精神的出走者,從初始的樸素的忠義孝悌,雖然流于扁平,又是土地的終極守望者而得到人物豐滿(mǎn)。他渴望掌握自己的命運(yùn),也渴望改變他人的命運(yùn)。他的身上背負(fù)的是近代以來(lái)的湘西民族文化的歷史。爹的人生與傳統(tǒng)政治文化自我瓦解的慣性態(tài)勢(shì)同頻。
四
拋開(kāi)文本的評(píng)論,我們回歸非虛構(gòu)敘事話(huà)題。爹的事實(shí)上就是這片多情苦難的土地的化身,爹的人生跌宕起伏,千轉(zhuǎn)百回;娘在苦難中不死,在癱瘓后能夠奇跡般站立行走都是生活的真實(shí)。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一次接受采訪(fǎng)中說(shuō),人們討論中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在馬孔多是真實(shí)的存在。在彭學(xué)明文學(xué)世界里的非虛構(gòu)事實(shí)上同樣是真實(shí)的存在。
在湘西和過(guò)去的老中醫(yī)或梯瑪、巴黛打過(guò)交道就會(huì)明白,他們所用的藥物和治療過(guò)程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用牢固的世界觀引導(dǎo)你潛在的力量,這是神對(duì)巫醫(yī)的誠(chéng)實(shí)與信賴(lài)回報(bào)的功力,也許就是神的眷顧。我不敢肯定。但我見(jiàn)過(guò)的湘西巫師都是因?yàn)楸嗟浇^望然后通靈的人,我敢肯定的是娘精神世界的形成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絕望和苦難的頓悟。這種頓悟暗藏生命的代價(jià),也只有微渺如同草芥的娘才能撐起的代價(jià)。從這個(gè)角度而言,娘又是一個(gè)湘西色彩豐滿(mǎn)的娘,精神的娘,豐滿(mǎn)厚實(shí)如同大地的娘,她與爹互為表里,構(gòu)成彭學(xué)明文藝美學(xué)思想的整體。
事實(shí)上,彭學(xué)明文學(xué)世界里爹娘的人生都在以道德的堅(jiān)守和苦難的承受的雙重形象在感召“我”的心靈,引導(dǎo)“我”的靈魂。然而,事與愿違的母親始終是母子戰(zhàn)爭(zhēng)的受傷者,我與爹的隔閡長(zhǎng)達(dá)漫長(zhǎng)的半個(gè)世紀(jì),甚至在母親消亡的一瞬也沒(méi)照亮“我”的心靈世界。雖其如此,然并非作為文藝評(píng)論者在對(duì)作品解構(gòu)之后的釋然,于我這個(gè)讀者而言并不為之感到悲哀,甚至體會(huì)到一絲溫暖。因?yàn)槲业闹庇X(jué)告訴我,《娘》和《爹》這正是一座精神大廈最終完成構(gòu)建的完美收官。因此,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作者彭學(xué)明早就明了然于心,頓悟在前。
用心閱讀一個(gè)作家的作品,可以窺探一個(gè)作家的成長(zhǎng)心路歷程和內(nèi)心隱秘。每一個(gè)人終將成為自己的過(guò)客,每一個(gè)人終將成為歷史,在迷霧一般的命運(yùn)里舉杯邀明月,對(duì)影成三人是孤獨(dú)的。我想這就以此句概括《爹》的文學(xué)魅力和《娘》出發(fā)的精神原鄉(xiāng),并致敬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