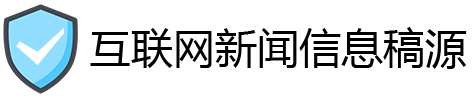伍珊珊
一切要從沈從文講起。
二十多年前,還是青蔥少年的歐陽文章沉浸在沈從文的小說世界里,被湘西這個(gè)“世外桃源”所迷醉,不顧親人勸阻,執(zhí)意來到湘西讀大學(xué),并最終留在了湘西生活。
在湘西的這些年,他始終熱烈地行走、探索、思考,而今,他將這些行走中遇見的人、事、物,那些熾熱的愛、奔騰的心、美好的青春等等付諸筆端,匯編成《湘西足履》一書。正如他在后記中所言:“《湘西足履》這本散文集于我而言是對(duì)自己生命過往的一次回眸,更是對(duì)湘西這片土地的深情致敬。”
于是,通過文學(xué)的筆觸,我們看見了他書寫的這片土地的歷史與未來、遼闊與細(xì)微、血肉與靈魂。
歷史與未來
“沅水,是一條歷史的河流。”
許是受了沈從文的影響,歐陽文章也愛水,尤其喜愛湘西的水。在開篇《沅水聽濤》中,他這樣形容河流于他的意義:“傾聽一條河流的聲音,宛如和一位孤獨(dú)的老人聊天,她會(huì)將整個(gè)生命歷程和盤托出。”在他眼里,沅水浸染著沉郁頓挫的憂郁氣質(zhì),是一條生命力澎湃的河流。
他寫河流,又不止于河流。坐在沅水邊聽濤的他,想到了湘西考古學(xué)家龍京沙,想到了友人,想到了屈原,想到了沈從文,想到了金庸,讀的時(shí)候,你會(huì)慨嘆他對(duì)與湘西有關(guān)的歷史典故的那種信手拈來與灑脫不羈。
而在《古苗河:流淌在生命深處的河》一文中,他看到的是一條浸潤(rùn)了幾千年苗族文化的河流,是一條見證了苗族悲壯的抗?fàn)帤v史的河流。他寫道:“它還是一條悲壯的河流,一個(gè)民族的血與淚、一個(gè)民族的傷痛與悲壯逆流成河,便成了我們身后的這條古苗河。”
在他的眼中,湘西的每一條河流都有其個(gè)性與歷史,湘西的每一座山、每一個(gè)村莊都有其獨(dú)特與精神。
正如湖南省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huì)主席田茂軍所說:“作為在湘西工作的異鄉(xiāng)人,文章對(duì)湘西的書寫往往有著‘他者’的獨(dú)特視角,這使得他有一個(gè)比較客觀的立場(chǎng),能保持一定距離來‘審視’湘西。”他稱贊歐陽文章的這些文章既充滿了文學(xué)的詩意,同時(shí)亦不乏理想的思考高度。
的確,在這些散文中,作者既是地理意義上的跋涉者,又是文化意義上的追問者,這種“步履不停”不僅是身體的遠(yuǎn)行,更是精神的溯源。他以步履為線索,將湘西的奇山異水、野性文化編織成了一部行走的史詩,讓我們望見了湘西的歷史與未來。
遼闊與細(xì)微
而對(duì)湘西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歐陽文章始終懷有一種悲憫的情懷。在那些遼闊的風(fēng)景之下,他的細(xì)微令人感動(dòng)。
他的書中既有對(duì)湘西普通匠人、歌者的細(xì)膩刻畫,亦通過他們的生命軌跡折射出楚騷傳統(tǒng)、巫儺文化與現(xiàn)代性碰撞的復(fù)雜圖景。
“作為一名司鼓,向敏謙掌握整個(gè)舞臺(tái)的節(jié)奏,當(dāng)然,也僅僅掌握節(jié)奏而已,沒有人能掌握它最終的命運(yùn)。”
“板凳上,滔滔不絕的陳啟貴說話費(fèi)力氣,汗水從額頭的皺紋里汩汩地冒出來。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屬于它的故事,這些故事,多半就潛藏在這些長(zhǎng)者深如溝壑的皺紋里。”
“歷經(jīng)興衰,如今,亭子關(guān)只剩一片廢墟。或許,在李祖興的內(nèi)心深處,祖祖輩輩在這座屯堡里血雨腥風(fēng)的掙扎歲月也已化成了一片廢墟。”
……
我在讀他筆下的這些人物時(shí),總會(huì)不自覺地跟隨他的腳步,與他們一起走進(jìn)那些被歷史掩藏的歲月。
面對(duì)現(xiàn)代化浪潮對(duì)湘西原生文化的沖擊,歐陽文章并未陷入單純的鄉(xiāng)愁詠嘆。他懷有一種清醒的憂思與克制的希望,他既批判“景觀化”的文化消費(fèi),又堅(jiān)信“步履不停”的傳承力量,他的書寫既保留了散文的詩性,又兼具人類學(xué)田野調(diào)查的深度。在浮沉的歷史中,在斑駁迷離的現(xiàn)實(shí)世界里,他總能撥開層層迷霧,以一名“異鄉(xiāng)人”的身份挖掘出那些故事與人,這也許出自他的本能,也許是他對(duì)這個(gè)世界善意的過濾。
作家蔡測(cè)海評(píng)價(jià)他:“他寫人物、寫朋友,足見赤子之心。他對(duì)人對(duì)物,對(duì)自然和時(shí)間,溫柔以待,善意敘述。對(duì)所有著文者來說,對(duì)世界的善意是必須的。”
我訝異的是《三進(jìn)茶峒 三悟〈邊城〉》中,他對(duì)自己內(nèi)心的剖析。在人生的遼闊中,他也敏銳地抓住了那些細(xì)微的情感。
從夢(mèng)見翠翠到“永恒的凝眸”,再到《等待戈多》,在“邊城”中行走的他,終于捕捉到了人生的細(xì)微之處。他寫道:“至此,我覺得,沈從文在《邊城》里講述的其實(shí)不僅是愛情,不僅是執(zhí)著,或許,他和塞繆爾·貝克特一樣,更多地講述了人類命運(yùn)捉摸不定的虛無、迷離、痛苦,甚至荒誕。”“我不再規(guī)勸翠翠停下她的等待,因?yàn)椋l也無法左右命運(yùn)的撥弄。”
于是,我們窺見了一個(gè)人思想成長(zhǎng)的歷程。至此,歐陽文章也已不再是當(dāng)年那個(gè)迷茫與執(zhí)著的他,他已然更加遼闊。
血肉與靈魂
“人世”篇章的那些文字,我愿稱之為這本書的血肉與靈魂所在。
正如作家龔曙光所言:“沒有對(duì)湘西土地的生命楔入,斷不會(huì)有如此深沉而慷慨、痛切而超邁的人性歌哭;沒有與湘西文化的生死糾纏,斷不會(huì)有如此專注而豐沛、樸拙而靈異的審美書寫。”
他飽含深情與懷念寫下與孫建忠老師的三面之緣,他滿懷落寞與恍惚寫下對(duì)老屋不復(fù)存在的失魂落魄,他寫下那些漸行漸遠(yuǎn)的伙伴給他的浮生若夢(mèng)之感,他寫下對(duì)書癡楊云磊的喜愛與褒贊,也寫下戒酒途中所發(fā)生的趣事,他寫一個(gè)湘西書店的寂靜生長(zhǎng),寫因夢(mèng)而生的思念親人之情,也寫下與詩人劉年的交往情誼,讀來無不令人動(dòng)容。
在《斷章》一文中,他寫道:“骨子里安靜了,才能從容;從容了,對(duì)這個(gè)世界就有了理解,有了包容。擁有了這些品性,再來面對(duì)這個(gè)世界,他便有了定力,便能靜下心來做他認(rèn)定的有意義的事情,不再為世俗所擾。”
所以,書寫湘西,就是歐陽文章認(rèn)定的有意義的事情吧!
在《湘西足履》里,他對(duì)散文也做了諸多的嘗試與探索。在他眼里,“真正的好散文應(yīng)該有真誠(chéng)的寫作態(tài)度,應(yīng)該遵循大道至簡(jiǎn)的規(guī)律,應(yīng)該有充足的文學(xué)性和創(chuàng)造力,應(yīng)該張揚(yáng)生命的獨(dú)特體驗(yàn),應(yīng)該傳達(dá)對(duì)世界的深刻認(rèn)知……”盡管他謙虛地說遠(yuǎn)沒有達(dá)到他的目標(biāo),然而我們看見了他的努力與真誠(chéng)。
《湘西足履》以步履丈量文化的厚度,以文字熔鑄精神的重量,在文化行走中不停地追問。當(dāng)歐陽文章行走在沈從文、黃永玉等先賢留下的文化路徑上時(shí),他既在續(xù)寫“湘西文脈流長(zhǎng)薪火傳之不熄”的當(dāng)代篇章,亦在探索一條屬于這個(gè)時(shí)代的湘西文化突圍之路。
山河遠(yuǎn)去,流水濤濤。生命不息,步履不停。
我們?cè)撊绾谓庾x湘西呢?散文集《湘西足履》或許能給我們提供一種思考——真正的生命敘事,永遠(yuǎn)在路上;文化的薪火,總在步履交替間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