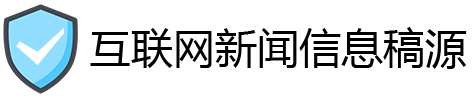——讀武吉蓉散文集 《歲月靜好》
謝慧
席慕蓉說,“故鄉的面貌是一種模糊的悵惘,仿佛霧里的揮手別離。離別后,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永不老去。”故鄉亦是很多人種植在靈魂深處那魂牽夢繞的朱砂痣,抹不去忘不了,伴隨你我看似短暫卻又漫長的一生。
武吉蓉筆下的故鄉情是色彩明艷、內容飽滿的,她和西門垅的緣分有60來年了。這是從她出生到現在回望“西門垅”的時光——厚重的,有趣的,豐富的,且不可復制不可替代的,屬于她個人如琥珀般珍貴的記憶,或許也是他們六十年代生人那一代人的關于故鄉記憶的縮影。時光逝去就不可追回,唯有文字的記錄是可以把每個人心中珍藏的故鄉人、風物民俗、美食美景等一一存留。
武吉蓉寫道: “我無憂無慮的童年少年時光是跟西門垅的伢兒玩大的。春天,我們三個一群、五個一伙邀到一起去山上挖胡蔥、掐蕨菜;螢火蟲飛舞的仲夏之夜,玩捉迷藏、騎高腳馬、跳橡皮筋;秋天出樅菌時,上山翻菌子、撿柴火;大雪紛飛的冬天,西門垅伢兒在巷子里堆雪人、打雪仗。”作者用細致、平實、溫潤的文字描寫故鄉人事,就像這幾位老友從記憶長河中緩緩走來,與她面對面閑聊,娓娓道來。
在武吉蓉筆下,故鄉湘西囊括了人生中所有相遇相知的有緣人和美好事物,并在這些人、景、事物之間,勾畫了一根受宿命牽引的“紅線”,看似貫穿了人生幾十年,其實又都有著親切親密而多樣化的情感關聯。
她寫明翠的父親張叔,天麻麻黑時,她的父親張叔先點燃一盆艾葉熏蚊子,晚上講完故事,會點燃一節樅篙油照亮。一個具有生活經驗且細膩溫情的湘西男人形象躍然紙上,讓讀者一下子就和這個人物走得很近,似乎從他身上也看見了我們父親的影子。
她寫明翠媽“會打苗鼓,有一套好看的苗服,過年過節走親戚才舍得穿。”還有瘦弱、說話細聲細氣,做事慢條斯理的張姑婆,據說過世時候,發現她的床鋪下藏了400多元解放初期的紅票子。她寫自己的母親也是不惜筆墨,“看母親手搓棉花,搖紡車紡紗,手拿梭子來回橫穿織布的情景……”就這樣,一個個賢惠能干、勤儉樸實的湘西女人瞬間走進了讀者的心里,產生了情感鏈接和共鳴,因為我們身邊有太多這樣沉潛于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了,她們有血有肉、可親可愛,一些看起來不起眼的生活小細節像一顆顆散落于時光塵埃里的珍珠,卻被武吉蓉擦去蒙塵、用文字一一串聯起來,散發出人性的光芒,再次熠熠生輝。
著名作家、魯迅文學獎得主陳應松說過,書寫故鄉是“重新喚起我過去的記憶,重新回到故鄉,書寫那一片我更加熟悉的土地,更加熟悉的鄉親。這是一種自覺的行動和應該承擔的寫作責任,作家是為故鄉而生的。故鄉是作家們寫作的源頭活水。”
由此可見,武吉蓉在她的這本新作《歲月靜好》里似乎也嘗試對自己的故鄉世界進行重建和構筑,擇選出能反映湘西人文、民風民俗、生存規律以及群居形態的故鄉人事,用自己擅長的文體記錄下來,特別是一些寶貴的正在漸漸消失的生活經驗——像《年味》《湘西人家的四季餐桌》等都可窺見一斑,這也是對故鄉情的一種“搶救式”的分享和記錄。我想,作為一個作家,她也踐行著自己的責任和擔當。當武吉蓉合上書本,再次深情回望故鄉湘西這片熱土的時候,心中一定是坦蕩且輕松的,百感交集也如釋重負了。
同時,在閱讀武吉蓉書寫的第二篇章《生活美》和第三篇章《人物贊》的時候,我品讀出了一位有著厚重生活閱歷的成熟女性身上所蘊含的善意、溫潤、睿智,如果說在第一篇章里武吉蓉還是一位負重的行者——因為記憶里承載著沉甸甸的故鄉人情和事物,那么,在生活美和人物贊的描寫中,她的筆調是輕盈的,是靈動的,更是客觀理性的。這應該是一位寫作者完成了對自我根源的探索之后,把筆觸放在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格局,從而在孜孜不倦的書寫中抵達了寫作更遠的彼岸。
我和作者武吉蓉相識于2017年11月,當時正是她讀毛澤東文學院第16期中青年作家培訓班的時候。時光荏苒,一晃就是七年。在這相識的七年里,我稱呼她為“蓉姐”。雖然并不常常見面,我們生活在兩座不同的城市,但氣味相投、靈魂有趣的人是不會走散的,關于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和現在即將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集,所幸,我都是見證者和參與者。或許這也是寫作帶給我們的鼓舞力量以及生生不息的好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