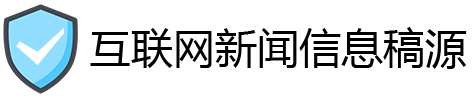龍駿峰
民盟先賢聞一多先生是著名的詩人、學者、民主戰士,2009年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聞一多雖以詩歌聞名于世,但他在民族歷史文化研究方面亦有極高成就。所著《伏羲考》一書,對中華民族起源歷史考據詳細,論證深入,其中一些見解發古人之所未發。特別是當中涉及苗族起源歷史的研究,許多論斷觀點新穎、見解獨到,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至今仍是“苗學”研究者們經常引用的主要文獻之一。《伏羲考》一書寫于1940年,寫作的主要出發點是為了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凝聚國人共識,一致團結抗日,但寫作興趣卻與聞一多20世紀30年代的湘西之行有很大關系。
1937年“七七事變”后,隨著日本侵華戰爭全面開戰,為避免戰火侵擾校園,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分別授函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要求三校在湖南長沙合并建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隨后國民政府又決定將其進一步搬遷到更偏遠的云南省,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次大遷徙從1938年2月開始,以長沙為起點,兵分三路前往昆明。第一路由教師家眷、全體女生和體弱男生組成,有的由粵漢鐵路坐火車到廣州,再從香港坐輪船到越南抵達云南昆明;有的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經柳州、南寧、越南入滇。第二路有馮友蘭、朱自清等教師10余人,直接乘坐汽車到昆明。在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是第三路,由200余名師生組成湘黔滇徒步旅行團,從長沙坐船到常德后,一路步行穿越湖南湘西地區,進入貴州,最后抵達昆明。
當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聞一多,正值不惑之年。他主動報名參加湘黔滇徒步旅行團,與其他師生一起從湖南徒步前往云南。這段旅程十分艱辛,但沿途風光民俗令人眼界大開,特別是在湖南境內,湘西地區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情給聞一多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來研究中華民族起源史時,將苗族作為重點研究對象。
據《聞一多年譜簡編》記載,1938年3月1日,湘黔滇徒步旅行團的師生們從常德的桃源縣開始步行。五天后,隊伍到達沅陵時遇大雪,不得不停留數日。當時聞一多的好友,湘西籍著名作家沈從文剛好回家鄉,居住在沅陵縣城的新居“蕓廬”里,得知老友滯留沅陵,便熱情邀請聞一多到家中住宿。《沈從文年譜》對這件事記錄詳細:3月6日,由長沙臨時大學一部分師生組成的徒步旅行團在向昆明轉移時路過沅陵,時暴風雨后又下起雪來,還夾著冰雹,旅行團只好住下。沈從文把聞一多、浦江清、李繼侗、黃子堅、許維遹等一些在旅行團中的師生請到“蕓廬”休息。沈從文也有憶述:“一多和旅行團到沅陵,天下起大雪,無法行進。我那時正回家,就設宴款待他們,老友相會在窮鄉僻壤,自有一番熱鬧。我請一多吃狗肉,他高興的了不得,直呼‘好吃!好吃!’一條毯子圍住雙腿,大家吃酒暖身。”
任葆華在《沈從文與聞一多關系初探》一文中說道:“沈當時還曾建議聞一多和他的學生搞苗人謠曲研究。”這說明,聞一多在沈從文家中暫住期間,沈從文為他詳細介紹了湘西的民風民俗,并向他提出了今后可以研究苗族歌謠的建議。沈從文是有名的鄉土作家,一輩子以書寫湘西而聞名于世,他既熟悉家鄉歷史文化,又在外面見過大世面,對湘西的認識和見解比當時的大部分人都更深刻。通過他的講述,聞一多收獲巨大。
聞一多在沅陵一共住了六天五夜。當時的沅陵,是除了常德以外湘西地區的中心城市,并且為苗族主要聚居區。六天時間,使聞一多先生對湘西、對苗族有了深入了解。3月12日,冰雪消融,旅行團繼續登程。受時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的委托,沈從文憑借與主政湘西的沅陵行署主任陳渠珍的良好關系,一路護送旅行團到芷江才辭別。從常德起始,聞一多先生一行人徒步穿越了桃源、沅陵、瀘溪、辰溪、懷化、芷江、新晃等地,所經之處均為苗、瑤、侗各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區,壯美的自然山水和瑰麗的民族風情豐富了他的見聞。
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后,聞一多一直主講詩經、楚辭、中國上古文學史和古代神話,其中古代神話研究為他后來撰寫《伏羲考》打下了堅實基礎。1940年10月,為躲避日軍轟炸,聞一多舉家搬到昆明北郊陳家營居住。隨后華羅庚也搬來,聞一多熱情地讓出一間房子給華羅庚居住,兩家“隔簾而居”。在這里,華羅庚研究數學,聞一多則開始著手苗族人文始祖“盤瓠”研究,進而寫成《伏羲考》一書。
《伏羲考》全書共有五個部分,分別是:引論、從人首蛇身像談到龍與圖騰、戰爭與洪水、漢苗的種族關系、伏羲與葫蘆。聞一多在寫作時都是單獨成篇,朱自清拜讀后,認為每篇相互間均有內在關聯,便連綴成書。該書通過考證伏羲、女媧為中華民族共同始祖和對圖騰崇拜的重新闡釋,從神話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多個角度來探尋中華民族文化源頭,構建出中華各民族同源同族的歷史譜系。聞一多寫作此書時引用的基礎材料,主要是苗、瑤兩族的原始神話傳說。他在“引論”中說:“目前我所有的材料僅僅是兩篇可說偶爾闖進我視線來的文章。”這兩篇文章,一篇是芮逸夫著《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另一篇是常任俠著《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對于這兩篇基礎材料,聞一多評價甚高:“前者搜羅材料,范圍甚廣。記錄著芮氏自己所采集和轉引中外書籍里的洪水故事,凡二十余則,是研究伏羲、女媧必不可少的材料。后者論材料的數量,雖非前者之比,論其性質,卻也相當重要。所載瑤族洪水故事,和漢譯苗文《盤王歌》一部分,也極有用。”
值得一提的是,聞一多撰寫《伏羲考》引用的這兩篇論文里面共搜集有25則與伏羲、女媧有關的神話傳說故事,其中湘西苗族的有4則,分別是《湘西鳳凰苗人吳文祥述洪水故事》《湘西鳳凰苗人吳佐良述洪水故事》《湘西鳳凰苗人儺公儺母歌》《湘西乾城苗人儺神起源歌》。若加上川南、貴陽、安順、廣西羅城、修仁等地的苗瑤原始神話傳說故事,光采用的苗族神話傳說故事就占了15則。
《伏羲考》通過大量論據,提出了伏羲、女媧是中華民族共同始祖,中國人以龍為圖騰崇拜主要起源于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傳說的論斷。特別是提出了湘西苗族崇拜的盤瓠、儺公儺母等人文始祖其實就是伏羲、女媧。這一論斷為后來的“苗學”研究者們打開了全新視角,對湘西苗族文化起源的歷史建構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伏羲考》最大的學術價值,是通過大量考證,得出了古代的華夏、苗蠻、匈奴、夷狄等各民族均為同源關系,雖然因為歷史、地理等原因發展成為風俗各異的不同民族,但從源流、譜系來說都同屬中華民族的結論。將《伏羲考》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聯系來看,聞一多當時所體現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尤令人敬仰。而他1938年3月的湘西之行,對這種思想的萌芽、成形和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潛在影響。